亚历山大·鲍罗夫斯基回顾,父亲大卫·鲍罗夫斯基在职业生涯中与留比莫夫等导演形成高度融合的合作关系,甚至在某一阶段难以区分导演与舞美的职能边界。这种创作中的“同盟”关系,成为其艺术实现的重要保障。
▲《伊凡诺夫》舞台模型
▲《伊凡诺夫》设计稿
他在舞台设计中的艺术实践,体现出深厚的象征性与整体性思维,其作品往往融合个人记忆、文化背景与戏剧文本,形成具有高度阐释空间的视觉语言。在《伊凡诺夫》一剧中,他摒弃传统布景中的家具设置,以“荒废庄园”为视觉核心,将枯枝与建筑重叠,构建出极具精神隐喻的舞台空间。
这一构思源于他在巴甫洛夫斯克庄园深秋时的记忆感受与视觉体验——透过花园的枯枝看到的建筑轮廓,并由此引发二维化的重叠视像,荒芜的场景传递出苏联知识分子在精神贫瘠时期的压抑状态。尽管主要演员起初反对在一个现实主义戏剧中没有任何支点,导演还是坚定地支持了大卫的设计,因为契诃夫曾写道:“欧洲人自杀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空间,而俄国人自杀的原因却恰恰相反。”最终仅添加两把椅子作为妥协,使该设计成为当代契诃夫舞台的经典案例。
▲《海鸥》舞台模型
在《海鸥》的创作中,大卫·鲍罗夫斯基将真实水域置于舞台中心,意在提供一种镜面,同时后半场中体现“水面结冰”的视觉转变,呼应剧中情感与氛围的骤变。该构思展现出他将自然现象转化为戏剧语汇的能力,其灵感也源自大卫·鲍罗夫斯基的多重记忆:一是童年时母亲提醒他小心折断冻成冰雕状的衣物的经历,二是在圣彼得堡河边目睹麻点公鸡冻于冰面的场景。这些生活片段成为其舞台意象的“储备库”,在此一设计中被激活并融入创作。
大卫·鲍罗夫斯基常将树枝的形态类比为人体的血管,或在建筑结构上制造“划痕”,以“破碎感”传递角色内心的分裂与痛苦。此类设计不仅拓展了舞台的视觉维度,更激发观众的联想与情感共鸣,实现戏剧体验在剧场之外的延续。
事实上,在尤里·留比莫夫早期作品中,塔甘卡剧院已在尝试今天所谓“沉浸式”的观演关系,如《震撼世界的十天》中,通过在剧场外街头开始制造革命氛围,剧场前厅设置革命歌曲演唱表演、红军装扮的检票员等元素,使观众在看戏前即融入戏剧情境。此种手法强调戏剧不应止于舞台,而应延伸至整个观演空间,与大卫·鲍罗夫斯基所倡导的“舞台引发联想”理念高度契合。
在契诃夫剧作的舞台设计中,大卫·鲍罗夫斯基表现出对空间、意象与戏剧精神的深度理解,其创作融合建筑环境、视觉艺术与文化记忆,形成极具象征性与整体感的舞台语言。
在雅典设计的《樱桃园》中,他巧妙利用演出建筑本身既有的14根黑色结构柱,以其暗示樱桃树。通过在柱体下端涂刷白色颜料,模仿现实中树木防虫刷白的行为,寥寥数笔即构建出樱桃园的意象。该设计被评论界誉为“切尔诺贝利时代的樱桃园”,木炭般的黑色的柱体与局部的白色形成强烈视觉对比,传递出焦灼与逝去之感,唤起观众对已消亡生活的复杂联想。观众席与表演区的布局亦强化了沉浸感,使观演关系如同共处于樱桃园中。
大卫在模型制作中强调作品的完整性与自律性。他主张“模型的背面若完美,正面必然无瑕”,要求连背面也要有完整的肌理。他认为设计不仅为呈现于观众,更是为了面对艺术家的自我。亚历山大在回顾父亲工作时,亦继承这一理念,注重模型正反面的整体制作。
在为多金剧院创作的《万尼亚舅舅》中,大卫以“干草堆”为核心意象,呼应剧中乡村生活被打破又最终恢复平静的叙事脉络。他设置三个悬置于空中的干草堆,到剧终缓缓落地将现实景物与演员并置,象征乡村宁静的重归。该构思融合了列维坦的画作《干草堆》与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将云喻为“云的枕套”的意象,兼具视觉诗意与戏剧节奏。该设计成功构建出契诃夫笔下“情绪戏剧”所特有的缓慢流淌的真实生活感。
大卫通过极简而富有文学隐喻的视觉符号,不仅构建出戏剧发生的物理空间,更深刻触及角色精神状态与文本内核,体现出其舞台设计作为“可阐释的视觉文本”的高度艺术价值。他在舞台大幕的运用中,赋予其超越传统功能的象征意义与结构价值,使其成为贯穿戏剧主题、空间结构与历史隐喻的核心视觉语言。
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樱桃园》首演百年纪念演出中,大卫·鲍罗夫斯基以该剧院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幕作为设计元素,大幕不再沿袭常规横向开启方式,而是逆向后退,形成视觉与心理上的“不可逆转”感。导演与设计者以此映射剧院自身辉煌不再的命运,与剧中樱桃园被拍卖的悲剧形成互文,强化了历史变迁与集体记忆的消逝感。该处理不仅在空间上实现多重幕布组合与迁换,更在精神层面构建起舞台与现实的双重叙事。
▲《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剧照
与父亲形成呼应的是,在亚历山大·鲍罗夫斯基以卫国战争为背景的剧作《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中,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个著名大幕进一步成为战争与和平对立的视觉载体。演出始于传统大幕场景,随后空袭警报、枪炮声骤起,幕布出现弹孔与破损痕迹,最终塌落为舞台背景的一部分,象征和平生活被暴力撕裂。幕布在此不仅是空间隔断,更成为战争遗存的“现场遗物”,持续提示毁灭与记忆的主题。
大卫·鲍罗夫斯基在设计过程中常为同一剧目创作五至六个版本,从中选取最具表现力且形式最简练的方案,强调“感受先于形象”的理念。他视舞台设计为思想表达的媒介,而非视觉装饰的堆砌。其对大幕运用理念非常典型地体现出这一追求:通过极简而强象征性的手法,实现空间、情感与观念的高度融合。
大卫与其同代设计师之间深厚的专业友谊与互相启发,也构成其创作生态的重要部分。他们彼此观摩首演、提出建议,形成一种集体共创的氛围。尽管当下戏剧创作节奏加快,此类深度交流渐趋稀少,但大卫所代表的那种注重思想性、象征性与整体性的舞台美学,仍对当代戏剧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卫的艺术生涯在晚年依然保持高度的创造力与探索精神。其生前最后一部话剧作品为2006年4月在圣彼得堡小剧院上演的《李尔王》,由列夫·多金执导。该剧筹备历时三至四年,大卫在创作过程中持续反思与完善,甚至曾在笔记中表达对作品未臻完美的不安。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质疑与追求中,其艺术表达愈发凝练而深刻。
大卫采用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结构语言,以交叉、倾斜的视觉构图构建出具有多重阐释可能的戏剧空间。他曾在创作初期以纸制草模型推敲空间关系,并因担忧正式模型无法再现草模中所捕捉到的张力与动态,最终选择以草模型为基础进行深化。这一过程体现出他对形式直觉与空间气质的敏锐把握,也反映出其创作中“感受先于形象”的核心思路。
从艺术风格来看,大卫的舞台设计呈现出两种相辅相成的路径:其一为运用带有历史痕迹与文脉的“现成品”,如旧式影院座椅、农具等,通过物件的真实感与叙事性构建舞台意象;其二则为如《李尔王》《哈姆雷特》中所见的抽象构成风格,以纯粹的形式与结构传达戏剧的精神内核。这两种路径共同展现了他在具象与抽象、叙事与象征之间的自如转换能力,并延续了苏俄构成主义的脉络。同时,重要的是这些因素的扮演或意指功能都远远超越了其本来属性。
大卫在舞台装置设计中展现出对空间、材料与意象的深刻理解,其晚期作品尤为注重装置的象征功能与视觉表现力。在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构建了一个以八根白色立柱为核心的舞台结构,这些立柱不仅作为舞会大厅的建筑元素,亦象征自然中的树干,兼具现实环境与精神指向的双重功能。立柱可旋转、倾斜,通过色彩与位置的变化呼应剧情发展:白色象征冬季雪景,黑色则在决斗场景中隐喻死亡,整体构成一种“视觉安魂曲”,既指向剧中人物的命运,也成为艺术家自身创作生命的回响。
在装置与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大卫始终强调“人在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常在模型中置入人物形象以推敲视觉与叙事关系。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虽未直接负责服装设计,但其空间构想已为人物造型奠定了基调,最终由服装史专家玛拉科娃协助完成,延续了其设定的色彩系统与戏剧氛围。
大卫亦善于运用真实物件作为舞台装置,以增强戏剧的现实质感与象征深度。在与导演多金合作的戈尔丁小说改编的《蝇王》中,他以“坠毁的波音飞机残骸”作为核心视觉元素,其装置构思准确捕捉到剧中文明毁灭与人性异化的主题。该设计最终获得采纳,并实际使用真实飞机残骸,延续了他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军用卡车等“现成品”中汲取灵感的创作思路。
大卫在舞台设计之外,亦通过装置艺术表达对历史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作品《悲伤之塔》是为纪念苏联成立74周年而创作,由74块集中营中常见的囚犯睡铺木板旋转堆叠而成,顶端放置了真实的集中营敲饭器具。该装置虽未实施,模型仍保存于家族博物馆中,成为对苏联时期集体创伤的视觉回应。
《悲伤之塔》在形式上呼应了构成主义的视觉语言,但在精神指向上却与塔特林的第三国际纪念碑歌颂、理想化的艺术叙事形成强烈反差。它揭示了大卫对民族历史中沉重篇章的反思与批判,体现出他从戏剧内容走向更广阔历史关怀的思想路径。其创作不仅关注剧本中的人物命运,更深入触及俄罗斯民族共同记忆中的伤痛与尊严问题。
大卫·鲍罗夫斯基的艺术观与精神气质深受其合作者与前辈影响,尤其是导演瓦尔帕霍夫斯基。瓦尔帕霍夫斯基曾历经集中营岁月,却始终未放弃信念与尊严,其即使在极端环境中仍保持衣着体面、佩戴领结的形象,成为大卫心中“精神尊严”的象征。瓦尔帕霍夫斯基不仅是大卫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更在文化信念与人格塑造上对其产生深远影响。他那种在苦难中坚守体面、在创作中追求高度的态度,成为大卫终身秉持的精神准则。
亚历山大·鲍罗夫斯基回顾了其父亲大卫·鲍罗夫斯基对他艺术道路与个人成长的深刻影响。尽管大卫生前言语不多、性格内敛,其存在始终作为一种精神参照,持续作用于亚历山大的创作思考中。亚历山大表示,自己在艺术实践中常感父亲“仍在身边”,会不自觉设想“若由父亲处理同一课题,他将如何展开”,并以此作为自我对话与方案推演的方式,形成一种内在的传承与延续。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三四年,两人的关系逐渐由父子发展为同行。大卫开始主动邀请亚历山大至工作室,分享讨论模型与设计方案。尤其在前往哥伦比亚布展前的九日共处期间,父子二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交流,亚历山大视之为“一生中迟来却完整的对话”。他特别提到,父亲从未直接给予表扬或批评,而是以“再想想”一类简洁的提示引导其独立思考,其态度往往需通过微表情或潜台词予以解读。这种含蓄而尊重个性的教导方式,塑造了亚历山大自主探索、自我教育的艺术成长路径。
大卫是一位始终沉浸于创作构思中的艺术家,即便静坐时亦持续进行内在的视觉推敲。他虽未直接指导自己的职业选择,却以其专注、自律且不轻易否定他人的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亚历山大的艺术态度与人格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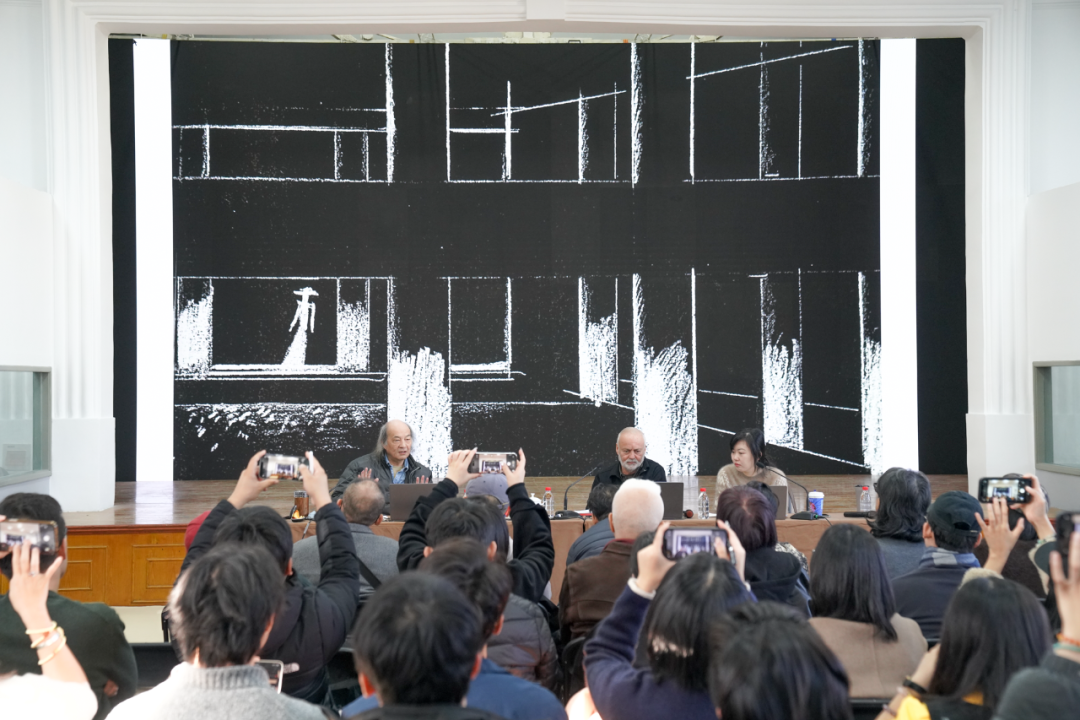
在总结大卫·鲍罗夫斯基的舞台艺术成就时,刘杏林教授首先援引了俄罗斯舞台史论家维克多·别列兹金的评论,其中指出:“大卫·鲍罗夫斯基的所有重要作品,都以垂直和水平的交叉的建造和材料结构,作为人类生命初始的原型: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内在与外界的冲突和对抗。换句话说,在鲍罗夫斯基作品的核心中,人们可以看到十字架,这是大地(水平)和天空(垂直)的古老语义符号。在20世纪的舞台美术史上,舞台空间的水平和垂直设计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属于美学上对立的戏剧潮流。早期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布景是水平结构的,西莫夫以及随后的“艺术世界”成员在其中重现了真实或风格化的场景。相反,戈登·克雷的舞台形象是从日常生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体现在垂直构图中。
20世纪下半叶,当这两种类型(垂直与水平)的舞台设计形式以各种变体共存时,每位大师都偏向其中一种类型。约瑟夫·斯沃博达倾向于垂直空间解决方案,这与布莱希特剧院的舞台美术家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坚定地站在地面上,并肯定功能性设计原则。人们还可以在俄罗斯舞台设计大师的作品中,看到对某种舞台构图类型的热情。爱德华·柯切尔金的作品是围合的,从水平到垂直的流动很顺畅。马克·基塔耶夫的作品开放、空间显露、复调且多成分,形成了一种舞台拼贴画面。丹尼尔·利德的设计尽管源于具体的尘世基础,由现实物质世界的物体构建而成,但它们一般都在向上发展,即指向人类生存的精神领域。大卫·鲍罗夫斯基将两种原则结合在一起:世俗与精神、粗放的散文与高雅的诗歌、文献与神话。这使得他的艺术具有了经典气质。”
刘杏林教授进一步具体指出,大卫的舞台设计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广泛运用“现成品”,如观众座椅、旧马车等实物,但这些物件在戏剧语境中超越其本身功能,通过表演与文本被赋予多重语义,成为可随剧情转换意义的符号;其二,擅长“抽象构成”,如在《哈姆雷特》中以编织网幕作为核心视觉元素,该结构既是秋千、王座,又是藏身之所与叙事清扫者,其意义随演出进程不断扩展,甚至超越创作者初衷,展现出强烈的阐释弹性;其三,始终坚持“剧场性与假定性”原则,其作品从不简单复制现实,而是通过高度提炼的视觉语言激发观众想象,在严肃题材中亦融入趣味与智慧,体现出戏剧作为“假定的艺术”的本质力量。
大卫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戏剧,尤其是现实题材与主旋律作品的舞台呈现,具有重要启示。他示范了如何以凝练、艺术化而非笨重写实的方式处理现实内容,使舞台不仅是背景,更是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其艺术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由于他始终触及戏剧的本质——即通过假定性与剧场性,实现演出整体与观众感知的深度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