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舞台艺术中,“材料”“空间”与“身体”不断覆盖、剥离与重组,它们共同决定了戏剧的生成与再分配,也决定谁能被看见,谁被遮蔽。约翰尼斯·舒茨的作品中,大量出现纯粹材料而非视觉物料,诸如木板、泥土、血、水、颜料、灰烬、沙、金属框、紧绷的线等,由它们,与演员的身体一同,在一个常常被限定的有型的可见的空间形内,共同组成一种顶格的视觉效果。
顶格,意味着每一个元素,包括一切散落和破碎在舞台上的残骸,都散发着绝对的精准。演员的身体,如同绘画中的形象出现在舞台视觉的画布上,赤裸的、瘫倒的、直立的、污浊的、浑身是血的形象,成为强大的力量存在。
一、在眩晕症中苏醒
“作为无前景的拟象,逼真的假象的形象突然像恒星那样精确,完全失去了其意义的光晕,沐浴在一种虚空的以太中。他们是若干纯粹的形象,是对现实的过分嘲笑。”
——让·波德里亚
约翰尼斯·舒茨的空间,是集中的筒镜。他常说,自己不关注风格、形式,更不想定义他的风格。他关注戏剧究竟要表达什么,舞台艺术始终在改变,一直在发展,设计环节应该带有开放度和包容度,把关注点放在尽可能准确把握对项目的理解。他会用一到两年时间阅读剧本,尽可能多地与作者讨论,与导演、与演员讨论,在排练中,结合演员与装置的作用关系,持续调整。

▲《The Homecoming》(2012)模型
在他的视角里,剧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模型,因此他非常关注模型的建立,每个剧作,他常常会制作四到五个模型方案,试图准确地复原“大模型”的场景。舞台设计是让空间诉说,从模型思维到物质材料,艺术家在空间与文本之间寻找系统表达的可能性。
模型是一个微缩的剧场,跟设计师的双手相比,它是更易于被转动的魔方,设计师通过转动这个迷你魔方来寻找解谜的最优路线。我们看到,舒茨的模型制作更偏向于手制而非数字制作,这就像帕梅拉·霍华德为剧目画出全部的角色形象一样。触碰是一个超越思想的动作,当我们的双眼接收到信息,脑子开始高速旋转,我们或许已经在一瞬间想到了结局,可是这仅仅是脑子里飘忽的概念,这种概念就像生日派对中的气球,令人振奋,喜悦,却飘在天花板下。但是触碰,触碰有时会作为飞镖戳破气球,发出吓人的响声,但也同时会扎在靶子上。触碰得多了,才能扎向靶心。
显然,像帕梅拉和舒茨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准确地扎向了靶心并且几乎百发百中。这类舞台艺术家之所以强调长跑式的前期探索,是因为你必须通过一种近乎笨拙的西西弗式的打磨,你的巨石才有机会获得一丝丝可能,走到它的目的地。这不仅是舞台美术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更是作为人应该如何存在。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或者在他制作作品的前期,包括在教学中,他都充分地展开关于社会、人、哲学、经济等多元问题的讨论。他说,创作必须考虑当下,在演出的当下,戏剧应该说些什么。这是阅读他的前提。
二、在深林里除草
在舒茨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清醒的道德感,作为舞台设计师,他主动压扁了舞台美术,使其变为坚实的地面,而演出在他构造的地面上肆意奔跑。


▲ 《King Lear》(2009)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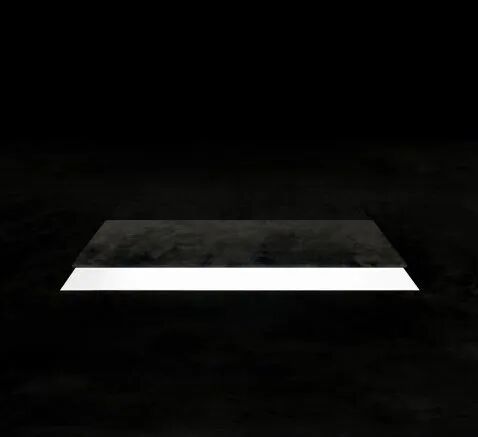
▲《Penthesilea》(2020)摄影
他只在乎那些他自身之外的东西,他放下明明本可以紧握着的吸引和赞叹,用尽全力把话筒归还给戏剧。他说,我的作品要非常实用,只做这部戏需要的东西,不需要的不用做。因此,我们看见了“仅存”,《夏日来客》(2004)里墙上平移的方洞;《李尔王》(2009)里瓦解的一条矮墙;《麦克白》(2005)里撕碎的一张白纸;《彭忒西勒亚》(2018)里隐出的一方白光,“仅存”随着演出的推进演出着,“仅存”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

▲《Three sisters》(2005)剧照
“将晦暗性归还于皮肤,因此也意味着归还肉身本有的坚实,从而避免将肤色仅局限为一道纱幕,虽然象征着形而上的光线,却又只能呈现神光的隐退。”
——莫罗·卡波内
约翰尼斯·舒茨与吉尔金·格施合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见一个接近抹平的空间与形象化的人共同在讲述一个事实。这些抹平的空间,无论是黑洞还是火柴盒,它们都坚决地使剧场的舞台空间挛缩到戏剧的内部结构,这种挛缩使观众不自觉地收紧视线,并且将人的形象有力地折叠进一种幽闭里。在幽闭中,演员被充分地保护和监禁,得以释放最强的能量,在幽闭中呐喊、爆裂、疲软,成为形象。形象是被抹平对立起来的,抹平打断了叙事,甚至使叙事永远不会被建立,它把形象孤立在舞台中间。而带有折叠权力的抹平又将权力转交给观众,观众的视线才能够像追光灯一样关注那些他想要聚焦的形象。

▲《Macbeth》(2005)剧照
在《麦克白》(2005)中,我们看到当雄心的纸张被撕毁时,野心的碎片遍布,构成无法重归于好的混乱。舞台上深深的漆黑模糊了后场形象的边界,好像他们正在沉入黑暗,或正在从黑暗中浮起。形象赤裸的肉身,在这部戏里呈现出衣装丢失的趋势,而非衣装的尚未出现,这份丢失好像让观众吃下失乐园的禁果,渐渐看清人类的原罪,又流转到人类坚持保留到最后的诙谐的皇冠。
对于人体而言,在最初,人们信仰那个“理型”结构,因此无论在古典主义的绘画还是雕塑中,艺术家都在努力复原“理性”的人体为何,当然经过几千年的争鸣,人的肉体被进行了部分的解放,甚至是解构,我们也好像看到了属于人的人类的身体。但是依旧,即使是在电影作品中,裸体始终作为一种视觉代表出现在人们眼前,进行表现和表述。在一些戏剧中,裸露的人的身体直观地呈现给观众,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观众的抗拒,这种抗拒或许来源于理想的余音,或是同为人的对于自我的畏缩。
2005年由瓦妮莎·比克罗夫特策划的一场演出,百名裸体女性面无表情地列队等待观众检视,吉奥乔·阿甘本的评述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于那些试图对裸体女性和参观者同时进行观察的人来说,他们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虚无之地。那些可能发生和本应发生的事没有发生。”阿甘本从神学层面在裸体-本性和衣服-恩典中进行了悠长的讨论,在《裸体》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关于表演活动里,赤裸的身体表现出的亏欠和无限。这种关系造成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形成了难以和解的状态,我们更难以阻挡观众的注视与洞察。由于表演活动本身就是具有方向性的强烈运动,观众对于裸体的注视完全可以嫁祸于观演本该流动的方向里,观众席隐秘的黑暗又助长了这静谧的暴行。
在20世纪初欧洲的戏剧作品中,艺术家们不遗余力地尝试用演员的赤身裸体把人“赤裸的肉身”释放出来。回到舒茨的《麦克白》(2005),正是由于在这部戏中观众得以“看清”原罪,这项原罪的重量直指观众,产生了常规观演方向下反方向的抗拒,这无异于从舞台上架了一台照向观众席的面光灯,打在所有人赤裸的脸上,驱散那些应有的暴力,让肉身出场。舒茨的众多作品都赐予演员以无花果树叶,他建造这座失乐园,将舞台上赤身裸体的演员回归到自然的隐秘的人类身体,让观众投以坦然地凝视。

▲《Anthropolis II / Laios》(2023)剧照
令人惊叹的《人类之城 Ⅱ》——《拉伊俄斯》(2023),舞台上唯一的演员莉娜·贝克曼无比自由,她在所有角色的灵魂中肆意地穿换,她像运动员在竞技场中战斗一样,坚定、机敏、充分、震耳欲聋。在这部戏里,舒茨给她准备了恰到好处的混沌、晦暗、暴力。张着大嘴的亢奋的希腊面具支在旁侧,作为一些注视人,把时间收纳回古希腊,而那头倒下的牛抓紧了危机和不寒而栗。在这样一个符号空间中,舞台美术脱掉了一切外衣,变成一个凝练的实在的功能性的匕首递给独角演员,扎进观众心里。
三、大理石像的行走
“真空是一种膨胀了的实体,而实体又是一种定位了的真空,现实也由此迸射出火花。”
——保罗·萨特

▲Francis Bacon绘画作品《Three Studies of Lucian Freud》(1969)

▲《Uncle Vanya》(2008)剧照

▲《Orestes》(2010)剧照
抹平的衬子让形象成为形象,而紧绷的无机框线又构造出一种充满紧张的透明。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2004)、《俄瑞斯忒斯》(2010)、《美狄亚》(2017)等剧目中,那个跳脱出平面的清晰和冷静,呈现出现实世界上完全不存在的或是人为的结构。这个结构把舞台变为坐标系,白色的线是矢量中数值的那部分,方向又是黑色的线赋予的。
线型结构作为撕毁现实的思想空间直指,把一切有组织的机理与色彩都消灭掉,形成了真正的真空,观众也被封锁在真空的外部,而由于现实世界的空气,真空体内承受着极端的压力,造就了令人窒息的紧张感。他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了属于戏剧的真实。舒茨在谈到对材料的控制时保持着极谨慎的态度。我们纵观他的全部作品,能看到一个艺术家与铅笔、碳条、色粉、油彩的嬉戏,如果不假思索地翻阅他的作品集,很容易读到近似文学性中字词的快速闪现。深邃的方盒子集中出现,悬线的板子,球体,线,玻璃展柜,墙的平面,门,希腊面具,漆黑,灰烬,各种各样的笔刷如同音符规律地跳跃,隐藏了一曲交响,但显然,我们可能无法听到,更难以听懂这场交响。
我们无法对舒茨的作品做任何笃定的接受,只能讨论,他的作品与大众是存在距离的,至少与我们的观众是存在距离的,然而这种舞台美术的隐没和疏离却保证了戏剧本体与观众的紧密。他还分享过一个出人意料的想法,他会使用一些制作结束后产生的废弃材料进行堆叠,试图找到适用于破碎边角料的加法原则,这让我想起他用枯枝败叶平铺的地面和用垃圾建造的围城。在《潘提拉先生和他的仆人马提》(2024)中,垃圾围城和无机的线性结构充分地揭开了潜在的差异与混乱。舒茨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对材料的把握,对空间的张弛,用具有现代性的语言完成对一个众所周知的情节的当代复述。

▲ 《Mr Puntila and His Man Matti》(2024)剧照
戏剧是必须被观看的艺术,舞台的每一次实验,都是在重塑观众的观看方式。面对当代剧场的多元审美——大型、前卫、激进、解构、——艺术家必然需要平衡艺术探索与观众感受。在舒茨的实践中,我们会关注到这种平衡。在他的作品上演时,他常常坐在剧院的咖啡馆,把自己浸泡在观众的讨论中,隐秘地感受观众的所思。而在创作时,就像《哈姆雷特》(2019)中,他使用了一个巨大的光球,一百五十个小钢球,以及一个悬吊的方形金属板,他谈到,就像这些元素,他希望是观众家里、阳台上随处可见的材料,并且是观众可以在家里动手完成的装置,这样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熟悉和亲密。他通过卸去繁复和技术,将观众拉进戏剧现实里。
事实上,即使大众娱乐已经彻底陷落进游乐场,但剧场就算处在冰河世纪也会为艺术精神设置保留席。舒茨的空间是精神的空间、思想的空间,在这些戏剧实践中,他去除了叙事线索,与观众进行拉扯。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传达,一种嘶鸣,在他构造的紧张与拉扯中,观众被卷入一场没有胜负的自由搏击。在优绩为王的时代,对于“绩”的确立过于有形。令人感动的是,在疯狂的戏剧艺术和疯狂的剧场里,也有一群疯狂的观众,他们宁可吃着馒头和花卷也要真金白银地购买高价席位,他们会拉长谢幕,久不离席。戏剧艺术的双手捧着微弱的火光在剧场的黑暗中摇曳,忽明忽暗,这点火光不能也不想成为壁炉里的熊熊大火,只为照亮,只为看清。
参考书目及注释:
1. 让·波德里亚. 论诱惑[M]. 张新木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莫罗·卡波内. 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M]. 曲晓蕊译.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5.
3. 吉奥乔·阿甘本. 裸体[M]. 黄晓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让-保罗·萨特. 萨特论艺术[M]. 韦德·巴斯金编. 冯黎明,欧阳友权译.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5.图1-6,8-10为约翰尼斯·舒茨作品,来源:约翰尼斯·舒茨官方网站
6.图7 为弗朗西斯·培根绘画作品,来源:WikiArt官方网站
本平台发布的文章,仅做分享使用,不做商业用途,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如果分享内容在版权上存在争议,请留言联系,我们会尽快处理。
作者:马艺涵(中央戏剧学院)
责编:张吉才
审校:赵 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