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展
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于2015年11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为总结理论成果并提升研究能力,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同期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作品集》和《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论文集》,以期反映近十年来中国舞台美术创作现状和研究成果。
今天,学会微信平台选编《中国第三届舞台美术展论文集》中的《论戏剧舞台的真实》一文,供广大舞美同仁交流学习。
对戏剧空间的表述,按照职业分工,自然应该是由舞台设计人员来建构的,但是在戏曲中,舞台设计者却有一个大的麻烦,即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剧本结构有着对戏剧空间表述的功能,并且任何舞台设计手段对戏剧空间的确切性表述,都将干扰其戏剧空间的自由转换以及戏剧空间与演剧空间的转换。
一 真实,文字的真实,文本的真实
汉斯·克里斯琴·冯·拜耳在《征服原子》一书中,有一段颇值得把玩的文字,转述如下:“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有一次对他的朋友汉斯·贝特说,他准备写日记:‘我不打算发表。我只是想记下事实,供上帝参考’。‘难道上帝不知道那些事实吗?’贝特问。‘知道’,西拉德说,‘他知道那些事实,可是他不知道这样描述的事实’”。
我不是基督徒,但不妨以上帝的存在而作一番假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自然知道想知道的一切“事实”,然而在利奥·西拉德看来,上帝却不知道其文字所表述的“事实”。
可见文字所书之事实,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由于文字这个“媒介”的介入,与那个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尽相同。
上帝尚且如此,何况我辈?
我们不是上帝,故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写下的事实、听到的事实、阅读到的事实,因时间、空间的差异,因人文背景的差异,因性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某种角度上讲,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只能是上帝眼中的“事实”的碎片。
对事件、人物、事物的记述最严谨的莫过于史书,然而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一书中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莫言先生套用这一句式对戏剧的评价是“所有的历史剧,都应该是当代剧”。
德里达们试图解决这样的困境。在解构主义看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由于阅读者的参与是一种必然,从而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是永恒性的存在,由此,德里达在其后的研究中发现,西方的哲学史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其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将“存在”置换为“在场”,因此德里达称西方哲学史称之为“在场的形而上学”。
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是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而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本意即是认知“真实”的方法,甚至其即是世界的本真。对于解构主义而言,对作品中的逻各斯的解构,在于对作品的所指面与能指面的区分。解构主义者对“阅读”的理解,是颇有意味的,他们着重于对能指——遣词造句的解读,而不是惯常的阅读者着意于对所指——叙事内容的解读,他们主张阅读者应积极介入作品的阅读过程,创造作品的意义。
解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几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用”。
着意于对语言形态的解读,而不是注重语言所叙述的内容,这让我们想起了魏晋时期的那场争论——“言象之辨”,以及争论的结果,即中国的士大夫们以“得意忘言”而为文化建构的主流方式。当然,我们还应记得孟子的“以意逆志”的阅读方式——“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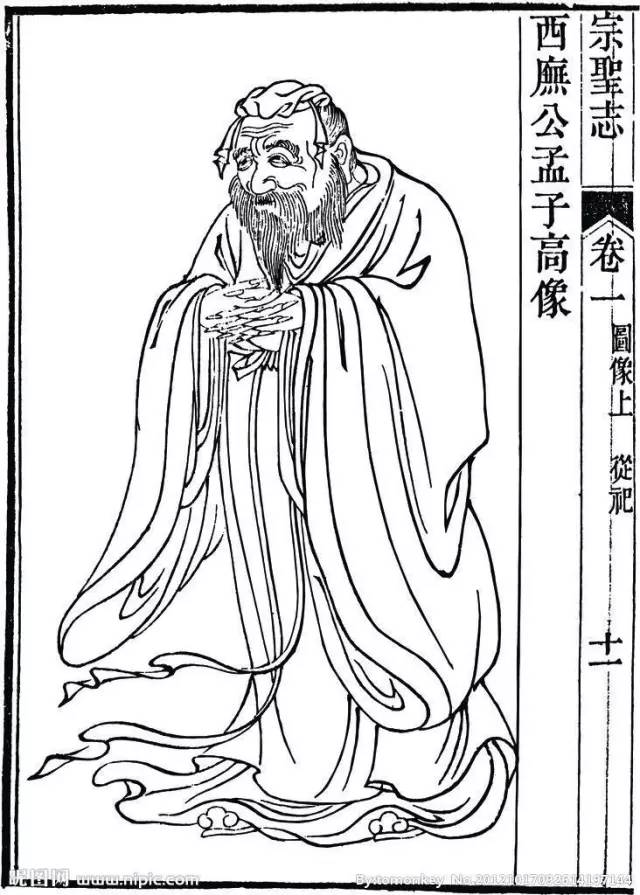
孟子像△
当我们把“得意忘言”的文本建构方式,以及“以意逆志”的文本阅读方式并置而对应于解构主义时,我们发现,解构主义者所努力解构并重组的工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得到过很好地解决了。文学文本的真实在魏晋时期便得到了确认,这样的传统使中国文学在中国人的心中几近取得了宗教的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艺术门类的价值取向与发展方向。
由此,对戏曲的研究直至上个世纪20 年代,只是文学艺术层面而非表演艺术层面。上帝所知道的真实,文字所表述的真实与文学文本的真实,中国人选择了文学文本的真实。

二 生活的真实与舞台艺术的真实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排演《大雷雨》的过程中,为了使演员获得真实感,请舞美人员制作可以注入水的桨,冀摇桨时的水声激发演员表演时的真实感,可见斯坦尼对真实性追逐的不遗余力。现实主义的戏剧原本便应着力于此。
同样是水与桨的舞台剧,却是另一番景象,19世纪20年代的一出《秋江》,舞美人员为其设置了一条番头船,老艄公与俏尼姑一段精彩的表现波涛涌动的表演,则由于船的真实的存在而显出戏曲表演者的矫情与做作。

秋江△
如山先生记录过一段史料:“我们看过杨小楼的一出戏,后头是一个山林的布景,可是他穿着很华美的衣服及厚的靴子,一个人在树林子外走来走去,一会到林子这一头,一会到林子那一头。按人走路不应该这样快,不知道他是作什么,后来问人,才知道是骑着马打仗,为什么打仗穿那么厚底靴呢?”①类似的景象在《智取威虎山》中也有,演员跑完圆场,已是跨过了万水千山,而写实的景却是纹丝不动,于是跑圆场的程式表演,让观众不知其在忙乎什么,程式表演成为儿戏。
 智取威虎山剧照△
智取威虎山剧照△
一幅写实的景片、道具足可以显现戏曲艺术的“假”。
一幅写实的景片、道具足可以毁掉戏曲艺术的“真”。
对于生活的真实与舞台艺术的真实,不同的价值观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选择无所谓对错,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之大、之繁杂,绝非一种观念所能包容得下的,重要的是文化观念要与艺术手段应合二为一。
在《沙田答问》一文中,黄宾虹先生对于东西方写生绘画有着这样的表达:“写生之法,须先明白各家皴法,如见某山类似某家皴法,即以其法写之。盖习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西画之初学者,间用镜摄影物质入门,中国画则贵神似,不必拘于形样,须运用笔墨自然之妙,故必明各家笔墨及皴法,方可写生。”
达芬奇对于绘画,则要求绘画者如镜子一般尊重所描绘的对象。
如果我们把国画的各种皴法以及“行当”的程式化语言,作为类型的概括方法,并成为文化的约定来认识的话,那么某一处的自然景象、某一个特定人物只不过是这一类中的这一个而已。熟悉皴法才可写生,并以类型化的皴法去写生,其目的是在这一类中,表现这一个,这是中国画的写生之法。我们可以将这个逻辑套用过来:只有熟悉“行当”,才可以去创造人物。如此,才能在这一类人物中,表现这一个。
导演不可以违背传统戏曲的建构法则,舞台设计者也没有权利违背这个建构法则。现在有些导演在导演戏曲剧目时,常常以斯坦尼的“体验说”要求戏曲演员体会剧中人物,这一做法,颇值得商榷。在传统戏曲中,当是先把握住“行当”,才可以进入“这一个”人物,一旦人物外化的形体语言与“行当”的形体语言发生冲突,则人物必须服从于“行当”的形体语言。

黄宾虹△
黄宾虹心中的绘画,画作与所描绘物象之间,除去工具、材料之外还有着一个介媒。达芬奇心中的绘画,甚至尽力消除工具、材料的存在。
黄宾虹先生所论述者,非特指于绘画,而是归纳文化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具体的文化建构方法。浓、淡、干、湿、焦的五色墨以皴、点、勾、勒、染的方法画出了大千世界、众生百态。
如是,戏曲演员的表演于角色,当是首先坚守生、旦、净、末、丑,行当约定的唱、念、做、打为表现人物的方法,其次才是对现时人物的观察、学习。
浓、淡、干、湿、焦的五色墨之于画家,生、旦、净、末、丑对于戏曲家而言,犹如厨子炒勺中的酸、甜、苦、辣、咸,五味调配得当、适度,即是一盘好菜。一盘炒凉瓜,好厨子以辣散其味,却不以糖伤其苦。一份鱼香肉丝,酸甜辣调配得当,食客便有食鱼之乐。前者的要诣在于用散的方法而弃对抗,后者的要诣则是以意生物。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人的一生不过是三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一是人与人的,再是人与内心的。三种关系的文字描述、论证,在现代的学术方式上,必然采取分开一一道来的方式,但在生命的过程中,三者圆融为一,无以剥解。味相偕而不对抗、以意生物的方法终究是“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另一种表达。
“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文化精神所建构的中国文化,对真实的记录、描述、描绘的缺陷是明确的,其缺乏与视网膜成像规律相对应的真实,其缺乏演绎逻辑推演的严密与深刻,而优势也是明显的,其较好地还原了生命状态,并确认记录、描述、描绘品自身存在的真实,从而赋予记录、描述、描绘品独立存在的品质。而中国文化优势得以呈现正是中国艺术中对介媒,对工具、材料的确认与运用,并将其升华为作品中不可分割的品质。
四 舞美的确指性与游离性
任何可以满足观演关系的舞台必然具有剧场性。对于剧场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我能尽力做到真诚,并尽力寻求真实,避免虚假,特别是剧场性的、匠艺式的虚假……”。

事实上,戏曲在演出过程中,空间形态是多个空间的重叠,这个重叠的空间,可以如现代戏剧般以并置而重叠,但其更长于以流动之法而使空间重叠。
更有意味的是戏曲时空观念,不仅是戏剧事件时空的自由转换,更有表演过程中自由地出离对戏剧事件的表现,而对当下演出进行确认。
(1)演出空间
戏曲演员与观众共有的进行戏剧活动的空间,即看戏、演戏场所之所在。
人类的戏剧活动,无论对于演员还是观众,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换言之,演戏与看戏的双方,都清楚进入这个场所的目的。但是不同的舞台样式、不同的观众席,对于观演双方而言,却有着不同的心理暗示。古希腊、古罗马的半环状、环状剧场所形成的观演关系,给观演双方以盛会的感受;镜框式舞台的剧场强调了相对严肃的“艺术”活动的特质;黑匣子的小剧场,其被涂成黑色的裸露的建筑结构以及非常接近的观演距离,给人以在幽密的空间中打开心灵的渴望;中国传统茶园中的戏台,其观演关系的设定给人以娱乐的感受;庙台子、野台子,则给观演双方以节日般的喜庆感。
不同的演出空间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暗示,这个被演出空间暗示出来的心理状态,在戏剧未开始之间,观演双方已经在等待相应的戏剧形态的出现,以满足被暗示出来的心理状态的需求。
(2)戏剧空间
当舞台上演员与演员进行交流而演绎于戏剧事件的时候,戏剧空间即呈现在这个舞台上,戏剧空间是对戏剧事件的说明与表述。
戏剧空间是戏剧演出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无论是否有物质性语言予以表述,只要大幕拉开,只要开场锣筛响,只要演员演绎于戏剧事件,这个假设的空间便在舞台上出现了。这个假设的空间可以通过再现性的舞台设计语言予以确切地表述,或者是以表现性的舞台设计语言予以的表述,当然这个假设的空间还可以以写意的设计语言予以表述。
以“虚戈为戱”的戏曲,自然并不掩饰其戏剧空间的假定性存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传统戏曲几乎是以空置的舞台,并通过戏曲演员的语言方式、程式化表演的方式以及符合化的砌末,从而让观众以感知的方式确认这个空间的存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虚幻性的戏剧空间的存在,使得戏曲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美。
然而,戏曲对戏剧空间虚幻性存在的认同与运用,却为舞台设计工作带来了麻烦。对戏剧空间的表述,按照职业分工,自然应该是由舞台设计人员来建构的,但是在戏曲中,舞台设计者却有一个大的麻烦,即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剧本结构有着对戏剧空间表述的功能,并且任何舞台设计手段对戏剧空间的确切性表述,都将干扰其戏剧空间的自由转换以及戏剧空间与演剧空间的转换。
舞台设计者之于戏曲的戏剧空间,无疑是尴尬的,若对戏剧空间予以表现,则阻碍了程式化表演,并阻止了戏剧空间的自由转换以及戏剧空间与演剧空间的转换;若不对戏曲的戏剧空间进行表述,舞台设计的工作,便只能是对供于演出的舞台进行装饰性的处理。
对于话剧而言,无论哪一种流派的话剧,这个尴尬是不存在的。对一个具体剧目的戏剧空间的表述,正是话剧舞台设计者着力之所在,无论是以再现性的或是表现性的设计语言,都会使得话剧的戏剧形式更加完整、完美,更加明确。
(3)演剧空间:
在戏剧演出过程中,演员脱离戏剧事件的情节,转而与观众进行交流所形成的空间。
演剧空间并非戏曲所独有,在西方诸多现代戏剧流派中,都会有效地运用演剧空间,以强化舞台艺术特有的观演关系的可互动性。但是从戏剧空间转化为演剧空间,再回到戏剧空间的过程,唯有戏曲运用的最自由、最自然、最从容,这种自由、自然、从容表现为空间转化过程的流动性。
演剧空间在戏曲演出过程中的产生,得自戏曲剧本中的设定,得自丑行的“科浑”。
这个空间的出现,以西方戏剧学的角度审视之,是为了阻断戏剧事件的自然延伸,颇近于布莱希特的“间离”,但传统戏曲对演剧空间的运用,则是为了舒缓观众在持续“看”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疲劳感,展现“虚戈为戏”的戱的本质。
更为重要的是两者的界阈不同,“间离”者的目的是使观者出离戏剧的演出而回到个体人的思考状态,戏曲观众的出离戏剧而回到演剧现场的当下。
固然,戏剧空间与演剧空间的转换,在演出中是由演员完成的,但是这个转换被观众认同,却绝不是简单的由演员的“唱、念、做、打”而可以完成的,这个转换的最终完成,需要对演出空间的形式美感有所约定,以促成观众的认同。
传统戏曲的演出过程自由转化于演出空间、戏剧空间、演剧空间之中,当我们回到西方设定的舞台设计这个语境下,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戏曲的戏剧空间是游离状态的,任何舞台设计师对其进行确指性表达,都会阻止传统戏曲对时空的自由运用。
五 意真与象假
“虚戈”的戱以假而为之,却成就了戏曲艺术的真。
“戱”是假的。其故事是假的,假到经不起生活逻辑的推演;其唱是假的,其用嗓既非生活,也非生活中的咏唱;其舞是假的,其既非生活中的常态下的动作,也非舞蹈之舞;其砌末是假的,其既非生活用具,又有生活的模样;其服装是假的,其既非当下服饰,也非事件主人公原本的服饰;其脸谱是假的,其戏剧空间是假的……构成戏曲的基本元素无一不假,而这个假却又有着生活的影子。

不假无以为戏曲;不假无以为写意;不假便不能生出真的“意”。
“戱”是假的,故不以现实之逻辑为构剧之法,而以演义、传奇、神话的思辨方式构其剧;“戱”是假的,故不以生活之语为对话之法,而以可唱之语为其曲,以可吟之句为其言;“戱”是假的,故不以日常之举手投足为其“行、动”之法,而以舞蹈代之;“戱”是假的,故不以真切、确实之物营构环境之景,而以装饰之法以为砌末;“戱”是假的,故不以所属时代时尚之服饰而为服装,而集中国历代服装以为其“行头”;“戱”是假的,故不以原面目示人,而以浓脂重彩表情态。
“戱”是假的。“戱”中的一切皆是假的,但却营构了戏曲这个艺术本体独特的真。戏曲这个艺术本体的真,真到了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来类比。戏曲之真,真到了唯一。
“戱”是假的。“戱”中所有一切的假,皆围绕真的“意”而设定其假。这种设定之法,老庄哲学是其“体”,魏晋美学以为“用”。
由真而假,由假而真的戏曲,构成了矛盾。
1 真的戏曲艺术本体与“虚、戈”的唱、念、做、打、服装、脸谱的矛盾;
2 真切的演出空间与假的戏剧空间的矛盾;
3 真的“意”与假的“象”的矛盾。
这三组矛盾构成了艺术形式法则最大的相反,若相成则必以形式美而为之。形式美在戏曲中是不可或缺的,在真与假的互换中,形式美犹如润滑剂一般,使得这个转化自由而从容。
或可这正是传统戏曲舞台设计的切入点。
注释① 《齐如山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