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D第三届国际舞美大师论坛——与大师对话”活动于2016年5月25日上午在天桥艺术中心举行。活动由中国舞美学会副会长、国际舞美组织中国中心主席刘杏林主持。参与对话的嘉宾有: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沈林,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韩生,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章抗美以及中央戏剧学院译审黄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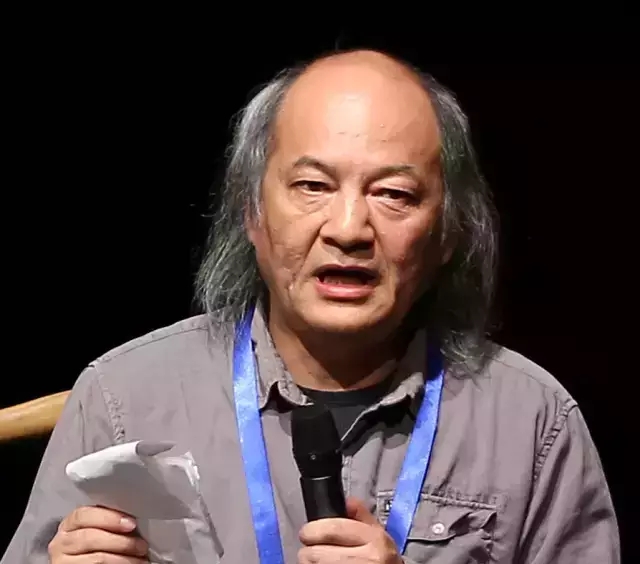
刘杏林作为学术主持率先提出三个问题:
1.在很多人看来,罗伯特先生的作品大多不以文本为基础,如果从这个出发点考虑,那么在创作中应该把握些什么呢?
2.像罗伯特先生这样知名的艺术家,在他的设计生涯中有很多历史文化和物质的条件来支撑,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
3.演员在罗伯特先生的戏里与传统戏剧完全不同,这些演员的价值是什么?

对于上述问题,罗伯特先生做出以下回答:
在我的作品中并不是不以文本为基础,文本很重要,但是我把这个重要性同样留给了其他元素,例如动作、光影或者布景等。我们都知道听和看的重要性是相同的,有时候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视觉元素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去聆听,光影也可以给我们一双眼睛,一对耳朵。所以很多人对我对文本的看法是有误解的。

对我来说,演员是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德国,传统方式的创作方法是所有人先坐在一起读剧本,然后再做排练安排,但是我并不这样。刚开始我会先调灯光,让演员任意做动作,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都习惯于传统的方式方法,所以演员经常因为没有动机而不知道怎么做,于是我会让他们把脑袋放空,慢慢地就看见有人做一些小动作,我觉得那就已经是一个创作的开始,然后我要求他们不断重复,或快或慢,就这样,在演员不断变化的动作中我找到了节奏和构图,逐渐地,一个新的作品就出来了。
紧接着,我可能让一个人读文本,让另一个人根据所听到的文本运动,这样不断重复,过了一两个月或者半年后,每个人就都有了文本。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就可以心无旁骛地研究文本了。有时我让工作人员关掉所有灯,然后静静地聆听文本。这时我能分辨出不同演员的声音,有高有低。声音低的演员我会让他放慢速度,声音高的演员我让他加快速度并在这个过程中加上音乐。
在我47年的戏剧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演员你应该怎么想。我给的提示都是形式上的,例如快一点,慢一点等。动作能否带上记忆性,文本能否带上外在性,能否把内在运动与外在语言配合起来是我思考的问题。我不会给每一个动作强加一种解读或者意义,我一直都是在这种开放形式下进行创作的。
解读文本并不是导演、演员或者舞美设计师的责任,而是观众的责任。他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反思和回想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这么说并不是代表我对我的作品没有任何感受,我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来与观众进行对话而不是把对话强加于观众。一个伟大的演员也应该是如此,他不会把自己内心的情感强加于观众,他会给观众留足空间。我的戏剧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戏剧,例如当我摸到手表上的水晶时我有一种清凉感;当我摸到自己的额头时我有一种温暖感,这就是事情原本的真相,但是我并不需要用语言去表达它,我用心去感受它。
在这种形式中,演员自己知道自己在表演,这就是真理。形式主义的作品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内在深深的感受到,另一种是外在的台词来表达。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自然主义的演员以自然的方式去呈现表演。我认为站在舞台上本身就是一种人为的动作,所以我们要诚实。如果我在舞台上做一个手势,那么它的重量与我在卧室做这个手势肯定不一样,这个分量应该把剧场的空间填充起来。

演员肯定是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我的戏剧生涯中,我希望演员避免自然主义。我的创作方式很自由:即兴、放空自己、慢慢做出动作。通过研究学习不断重复,到最后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就会符合我的初衷。我在即兴的基础上研究它的规律,这个即兴的过程就是创作过程,不断重复,让它变得自由。卓别林对于一个场景的镜头可以拍摄250次至300次,第一次做完必须不断重复,是因为没有重复就不能自由地掌握。例如今天早上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在和他的父亲学习骑自行车,开始他很害怕,通过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动作,慢慢的他就变得熟练,动作娴熟之后才有了自由空间去创作更多的可能性。

用造型艺术做戏剧,这是罗伯特•威尔逊的作品给沈林的最深印象。沈林讲道,戏剧是看的,还是听的,这是一个老话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戏剧是诗画的结合,如何处理这两个关系,罗伯特有自己的突破和探索。沈林认为,戏剧的未来好像是属于舞美的。
沈林问道:威尔逊先生的《聋人一瞥》在当时并没有文本,但是现在的作品基本都有文本了,例如《沙滩上的爱因斯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等。但是《沙滩上的爱因斯坦》中的文本又与后来所创作剧目中的文本大有不同,我想知道对于这种转变您是如何考虑的?

罗伯特•威尔逊答道:在我看来没有绝对的无声,即便是在无声的环境里也是无声胜有声的。例如我之前做过的那些荒诞剧,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本质是一样的。我聆听无声的环境,但是我不会去问这个意义是什么。就像听鸟叫一样,我们只会觉得它好听,但是不会去问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的文本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所以在演出中演员可以暗示一种情绪或态度但不是把表达强加给观众。一个手势,一个动作都是有声音、有意义的。我认为所有戏剧的视觉语言和动作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韩生表示:罗伯特•威尔逊先生这次的讲座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次戏剧观念上的启迪。1978年中国戏剧界有过一次戏剧观的大讨论,当时的讨论集中在戏剧方法。现在,我觉得我从威尔逊先生的讲述中获得的启发是,他是在思考戏剧的本质:戏剧是什么。要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因为对他来说,他去看了百老汇不喜欢。然后看到一个黑人小孩和一个警察的故事,触发他开始做戏剧。
他的戏剧动机是出于自身的精神需要。因为在中国目前已经有严格的戏剧定义,包括有严格的分工:文本、导演、舞台设计等等,各自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方面,罗伯特•威尔逊先生把它一体化了。他的写作特别强调观众,写作的完成是由观众最终完成的,由观众各自完成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这是我获得的启发。

罗伯特•威尔逊说道:我们的思想本身就是自由的,没有人应该给我们的思想罩上一层监狱似的东西。无论是在一个集权式的国家,还是自由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自由的。作为戏剧,我们应该给观众这样的一种自由,让他们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去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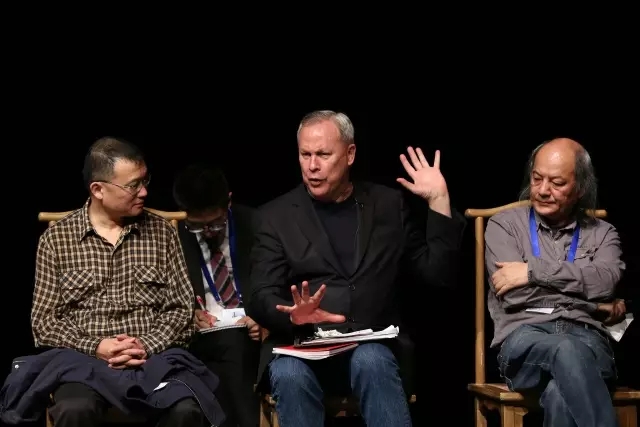

罗伯特•威尔逊先生给李六乙的最大启发是,他对于所有戏剧门类平等的看法。李六乙称,在我们戏剧史里,要么特别强调文本,文本作为唯一,要么特别强调导演作为唯一。要么现在有钱了,舞台美术作为唯一。每一个部门都想说话,但是真正的缺失是:观众不说话。
罗伯特•威尔逊真正重视的是观众,李六乙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未来的戏剧发展其实有很好的启示,不是以“我”为最大。此外,罗伯特•威尔逊的自由观:在极大的局限中去形成自由,李六乙对此表示认同。
李六乙向罗伯特•威尔逊问道:任何艺术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和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在西方历史中哪一位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对您影响最大?

罗伯特•威尔逊答道:可能是苏格拉底。他说过:“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是知道一切的,只不过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才逐渐开始学习的过程。”婴儿出生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但是眼珠在转,这说明他在做梦,但是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就需要去慢慢学习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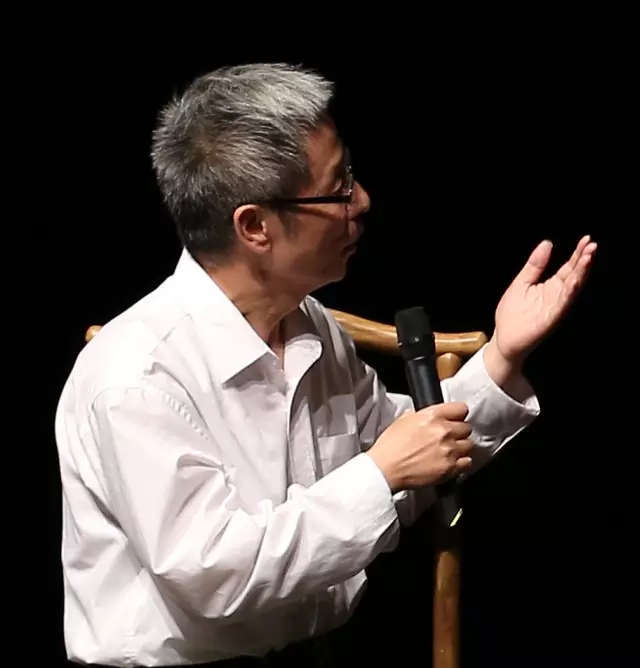
章抗美分享了个人对罗伯特•威尔逊舞台设计的观感:在他的舞台上,从最早的成名作品开始,就有动物。有时候是人造的动物,有时候是人演的动物,有时候是真的动物。一般戏剧舞台上不能用动物,也不能用婴儿。当今的戏剧舞台上,用动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罗伯特•威尔逊较早实践,应当说是一个引领者。


黄觉是罗伯特•威尔逊多本著作的中文编译者,她向罗伯特•威尔逊提问:威尔逊先生不给观众强加意义,要给观众留出足够的空间去理解。在翻译其作品时发现,很多线索和信息都是被隐藏起来的。观众有没有可能因为给的信息太少而无法解读作品呢?


罗伯特•威尔逊说:我觉得空间大了,意义才会更大。有时候我半个小时说一个字的力量会远远高于我一下子说好多话更有效果。


“与大师对话”活动结束后,中国舞美学会会长曹林总结道:正如李六乙导演所说,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个性化的思考,植根于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创作实践。中国舞美学会举办大师论坛,旨在搭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让各种观点都在这里发声,以期丰富中国当代舞台艺术的创作。
曹林会长寄语舞美工作者,在艺术实践的同时加强理论学习。在以往相当长的时间里,舞美人更多关注舞台实践,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理论研究,舞美学会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会员提供更多的学术交流契机,激发舞美行业的深层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