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句在看完由他执导的北京人艺版的《樱桃园》后,却变成了对自己的诘问,竟至难以成眠。

一、北京人艺
中国首家把契诃夫“四大名剧”搬上舞台的剧院
1903年的早春,契诃夫开始着手写他此生最后的一部剧作《樱桃园》。作为医生的他,已感知到生命的大限即将来临,他对自己的写作愈加严苛,原定3月底脱稿,却直至秋天才最终写完。自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由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演,迄今,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仅次于《哈姆雷特》每年都有演出记录的经典剧目,而契诃夫也被公认为是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从此,“作为戏剧家的契诃夫几乎掩盖了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早在上世纪40年代,焦菊隐先生就慧眼识珠,率先翻译了契诃夫的戏剧代表作《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这或许为北京人艺与契诃夫作品结下不解之缘埋下了最美妙的伏笔。
6月16日,随着李六乙导演的这版《樱桃园》的上演,北京人艺也成为中国第一家将契诃夫四大名剧(《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搬上舞台的剧院。为了呼应这桩剧坛盛事,与北京人艺毗邻的商务印书馆同步推出了同名图书《樱桃园》。书中除了翻译家童道明先生翻译的剧本之外,还收录了与契诃夫同时代并最早排演此剧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和剧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契诃夫夫人克尼碧尔等人对此剧的相关评述,以及李六乙的导演手记与濮存昕的表演体悟。这无疑有助于观者在走出剧场后,仍能在阅读中品咂契诃夫剧作的每一处细节的余味与深意,从而强化对于舞台上的《樱桃园》的审美感受,让经典真正沁入心灵。
二、“樱桃园”的消亡
心灵世界精神家园的消亡

《樱桃园》的剧情围绕着一座有着樱桃园的贵族庄园的归属展开,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却始终被戏剧界公认为最难理解的剧本之一。排演这样一出经典剧作,不啻为一次戏剧上的冒险与挑战,对此,李六乙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他在“导演手记”中写道:“一百多年来,契诃夫一直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像一个影,随风而至,润物细语。感而切肤之亲;疏而大隐于体;嗅而闻香识人;思而悲物痛绝。对他浩瀚思想的研究,犹如对伟大的莎士比亚,可以成为一座图书馆。因而,他的戏剧,他的人,所生活的日常生活的日常化,如我们所不曾看到的自己,成为了戏剧舞台生活的‘最难’”。“怎么将这种‘陌生’的生活日常化,并以不失超越语言文化关系的思想的哲学的意义”呈现于舞台上,就成了他此番导演中艺术上与思想上的双重“冒险”。这样的“冒险”意欲通向“我们永恒的生活真实”,直抵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为此,他在舞美、音效、节奏、表演等诸多环节的处理上渗透了他的所思所想,完整地表达了他对这部经典剧作的独特理解。

整部戏在一个封闭的舞台空间中进行,纯白色调的舞台由5个平面构成,呈现出极强的透视感。灯光映射下的特殊光影、斜坡上错落的几把椅子,简约地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衰败与破落;身着白衣的演员从始至终地随着剧情的铺展或静止或流动于这个封闭的空间,每个舞台瞬间都犹如一帧极具东方意蕴的美术作品,呈现出精致、唯美、诗意、凝重的戏剧效果。如此独特的舞台设计,抽离了剧本中的时间与空间,使“樱桃园”在具有了鲜明的象征性的同时,也让演员的表演空间具有了使原本“陌生的生活日常化”的熟悉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从而在演员们如同生活般自然的表演诠释中,不露痕迹地承载了导演对于“樱桃园”所寄予的超越时空的文化寓意与思考引领:“一个庄园,一个美丽的家,一段童年般美好的过往”也可能意味着“随着文明的进化,必将消失的一种历史必然”、“一种失去永恒的短暂的美”、“一种行将消逝的生活方式”、“生命进化过程中的生与死”、“生命意义的某个独特瞬间”,乃至“就是我们自己”。作为“自我精神现象”的心理呈现,它只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樱桃园’”,“‘樱桃园’的消亡,就是自我心灵世界精神家园的消亡”。如此纷繁多维的联想与心灵触碰,在演员舒缓从容的表演引领下,自然而然地滑过观者的脑际,像一首弥漫着忧伤的长诗,激起些微的痛的涟漪。
三、叙事节奏的放缓与停顿
李六乙与契诃夫的相契
将原本情节近乎沉闷的剧本,在戏剧叙事的节奏上再度放缓,不断地停顿,不可谓不是非常李六乙式的又一个大胆的“冒险”。这不仅对演员的内心的强大与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观众的专注力构成了考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之一——丹钦科曾就契诃夫剧本对话中经常出现的“停顿”,有如下的体会:“越接近生活,就越可避免旧剧场所特有的那种纯粹‘文学性’的流畅……我们要用属于生活本身的最深沉的停顿,要用停顿来表现刚刚经历过的纷扰之结束,用停顿来表现一个即将来临的情绪之爆发,或者,暗示一种紧张力量的静默。”可以说,契诃夫的这种无声的语言不是空白,不是停滞,而是人物感情最复杂的瞬间。停顿的表面是静止的,而人物的内心却翻江倒海。这种静水深流般的停顿所带来的内在张力,在卢芳扮演的女主角贵族柳苞芙的身上,有着令人惊艳的表现,撑起了全剧饱满的情绪底色与悠长诗意。这样的“冒险”,只能令人慨叹:这是导演与契诃夫心灵的“深深相契”。
尤值一提的是,濮存昕扮演的新兴商人罗伯兴,在买下庄园后的一长段独白的表演,于收放自如中,将扬眉吐气中的不自信与在真正的贵族庄园主人面前无法彻底摒弃的卑微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对于柳苞芙的暧昧情愫的表演分寸的拿捏,与他对瓦丽雅情感上的若即若离的处理,令人服膺。扮演老仆人费尔斯的李士龙,一出场,其深厚的台词与形体功力就牵动了所有观众的视线。青年演员雷佳扮演的大学生,将剧中附着了契诃夫对俄国知识分子热衷空谈而匮于行动的批评,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的几段著名的台词段落的表演,亦张弛有度,数次掀动了舞台的情绪高潮。唯一稍感不足的是,寄予了契诃夫对未来的希望的安尼雅,未能跳出几位戏骨的气场,成为剧中那抹原本夺人的亮色。
四、将契诃夫的悲悯责备
化为人艺舞台上的警醒
近三个小时不疾不徐的舞台叙事,似乎在为某一刻的爆发积蓄能量。当剧中人带着各自的命运渐次退去,那位似乎被遗忘了的、一生昏聩、安于为奴的老仆人费尔斯面向观众,道出那句被李六乙写在舞台后壁上方的临终之言:“生命就要过去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一段静默之后,由远及近,传来了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在契诃夫的剧本中,这一刻即幕落。但对于特立独行的李六乙来说,却在这一刻,开启了他的另一次艺术“冒险”——在长达3分钟的巨大轰鸣中,原本封闭的舞台豁然裂开,观众目睹了舞台被“拆毁”的过程。三个小时的沉闷,在这一刻石破天惊,山崩地裂,犹如一记重拳,击打在观众的心上,让昏睡者愕然醒来。这让我想起高尔基评述契诃夫作品的那段话:“他们中有许多人美妙地幻想着两百年以后生活会多么美好,但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朝思暮想,有谁来使生活美好起来呢?在这一长列垂头丧气的无聊烦闷的灰色人群旁边,走过一个伟大、睿智、对一切都关心的人。他对祖国的那些无聊烦闷的居民瞧了瞧,便露出忧郁的微笑,内心和脸上充满了绝望的悲痛,用温和的但又是深重的责备声调,恳切而动人地说:‘先生们,你们的生活过得太丑恶了!’”
我以为,李六乙的“冒险”结尾,将契诃夫这一饱含悲悯的责备,化为人艺舞台上的一个响亮的警醒: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逝,我们生活过吗?
舞美印象 牛春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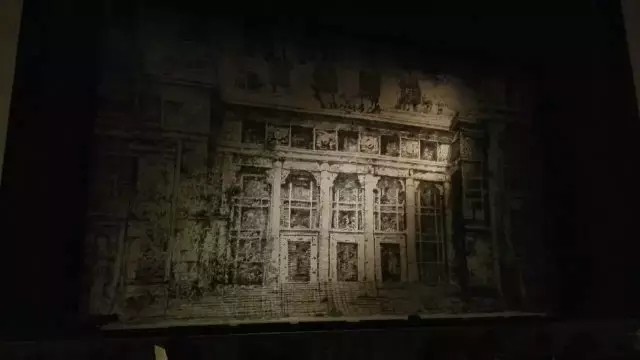




李六乙版《樱桃园》大幕拉开时,颇为极致的舞台给人很强的个性色彩。
米白色半倾斜的舞台上,穿着纯白或米白色服饰的演员或坐或立其中。白色的舞台原本是给人空旷的感觉,可这个前宽后窄的舞台,没有上下场门,除了面向观众席的一面外,其他五面都是完全封闭的,让人倍感压抑。
不过,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纯白色调的舞台,灯光映射下的特殊光影,斜坡、错落的椅子,甚至静止或移动的演员,都让观众如同看到了一幅幅美术作品,更体现了干净、纯粹的戏剧效果。导演李六乙同时也是这部戏的舞美设计,“我没有为演员设计具体的生活环境,设计的是角色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有很多确定的东西和不确定的东西,让演员能有更好的发挥。”
配合舞美,整台演出的灯光也别具一格,李六乙标志性的移动灯光再次出现。灯光设计方义表示,戏中很多新的灯光设计理念是第一次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呈现,“观众看后会发现,我们没有强调真实的时间,白天或者晚上,灯光的变化都是靠冷暖来区别,看上去很美,这也是导演对舞台整体美感的追求。”
为了挽救一座即将拍卖的樱桃园,女主人从巴黎回到俄罗斯故乡。一个商人建议她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出租,女主人不听。樱桃园易主,新的主人正是那个提建议的商人。樱桃园原先的女主人落下了几滴眼泪,走了。落幕前,观众听到“从远处隐隐传来的砍伐树木的斧声”……这就是契诃夫的《樱桃园》。
从《樱桃园》这部戏可以生发出种种不同的题旨来。在贵族阶级行将入木的20世纪初,由此可以反思到“贵族阶级的没落”;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十月革命后,由此可以导引出“阶级斗争的火花”;而在阶级观点逐渐让位给人类意识的上世纪中后叶,则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樱桃园的消失”中,发现了“人类的困惑”。
“困惑”在哪?美丽的“樱桃园”终究敌不过实用的“别墅楼”,几幢有物质经济效益的别墅楼的出现,要伴随一座有精神家园意味的樱桃园的毁灭。“困惑”在趋新与怀旧的两难选择,“困惑”在情感与理智的永恒冲突,“困惑”在按历史法则注定要让位给“别墅楼”的“樱桃园”毕竟也值得几分眷恋,“困惑”在让人听了心颤的“砍伐树木的斧声”,同时还可以听作“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樱桃园》里包裹的那颗俄罗斯困惑的灵魂,像是升腾到了天空,它的呼唤在各种肤色的人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其中自然也包括我们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
五十年代末,旅欧华人作家凌叔华重游日本京都银阁寺,发现“当年池上那树斜卧的粉色山茶不见了,猩红的天竹也不在水边照影了,清脆的鸟声也听不到了。”而在寺庙山门旁边“却多了一个卖票窗口了”。告别已经成为营业性旅游点的银阁寺,凌叔华女士在她的散文《重游日本》里写下了自己的“心灵困惑”:“我惘惘的走出了庙门,大有契诃夫的《樱桃园》女主人的心境。有一天这锦镜池内会不会填上洋灰,作为公共游泳池呢?我不由得一路问自己。”
有《樱桃园》女主人心境的,并不非得是女性,也并不非得熟悉契诃夫的剧本。五十年代中期,当北京的老牌楼、老城墙在新马路不断拓展的同时不断消失与萎缩的时候,最有契诃夫《樱桃园》女主人心境的北京市民,我想一定是梁思成先生了。
时代在快速地按着历史的法则前进,跟着时代前进的我们,不得不与一些旧的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纪之初,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迎接新的“别墅楼”拔地而起,同时也每天都在目睹“樱桃园”就地消失。我们好像每天都能隐隐听到令我们忧喜参半、令我们心潮澎湃、也令我们心灵怅惘的“砍伐树木的斧声”。我们无法逆“历史潮流”,保留一座座注定要消失的“樱桃园”。但我们可以把消失了的、消失着的、将要消失的“樱桃园”,保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只要它确确实实值得我们记忆。大到巍峨的北京城墙,小到被曹禺写进《北京人》的发出“孜妞妞、孜妞妞”声响的曾为“北平独有的单轮小水车”。
谢谢契诃夫。他让我们知道,哪怕是朦朦胧胧地知道,为什么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我们,心中会有这种甜蜜与苦涩同在的复杂感受;他启发我们进入21世纪的人,和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上倘佯,要懂得惜别“樱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