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四十载风雨同舟,四十载砥砺前行,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发展历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四十年来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在一代代舞美人自身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影响力与日俱增。
值此之际,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微信平台将推出“四十载四十人”特辑,选取对中国舞美发展历程中起到重大作用、有深远影响的四十位当代舞美大家,持续推出系列专访内容。
经过四十载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诸位舞台美术家前辈先贤为吾辈今时今日的继承发扬、开拓创新打下了尤为重要的坚实基础。记录第一线舞美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与实践经验,梳理学会发展脉络——这些整理工作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2021年5月6日,惊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李畅先生辞世,业界无不扼腕叹息。作为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李畅老师为推动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以及中国舞美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日,我们以此文深情缅怀李畅老师,同时拉开“四十载四十人”特辑的序幕。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主编 赵妍
先生生平
李畅,1929年出生,别名李道善,安徽合肥人,擅长油画,舞台美术设计,1949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同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李畅先生即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任舞台设计,后任中国青年文工团舞台设计。1953年参加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筹组,并任教舞台美术系,先后任讲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术委员、系副主任,以及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同时担任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1993年,李畅先生从中央戏剧学院离职休养。
李畅先生是新中国现代剧场建设的奠基者,新中国剧场技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畅先生自1952年即担任文化部剧场建设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承担了北京天桥剧场、首都剧场、人民剧场、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剧场、中央戏剧学院剧场等剧场工艺设计。作为国家大剧院工艺专家组组长、艺术专家组成员,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剧场建筑设计咨询顾问,先后参与了世纪剧院、保利剧院、新长安大戏院等30余座剧场的建设咨询工作。
李畅先生是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自演出场馆设备专业委员会成立,李畅先生即担任副主任,并指导剧场工艺组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先后参与了解放军歌剧院、北京二七剧场、国家话剧院、东莞大剧院、北京舞蹈学院剧场、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等剧场的设计咨询工作。
李畅先生的一生,在教学、舞美设计、剧场建设、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舞台设计:舞剧《和平鸽》,歌剧《白毛女》,话剧《桃花扇》、《上海屋檐下》、《屈原》、《原野》、《大雷雨》、《朱丽小姐》、《四川好人》、《拉曼卡人》,京剧《红灯记》、《战洪图》、《刘志丹》等。
油画作品:《密西根大街》、《小池塘》、《禄雪》、《农场》等。
出版著作:《李畅油画 水粉画选集》、《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永不落幕》,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
以下为李畅先生访谈实录:
(提问:学会记者 回答:李畅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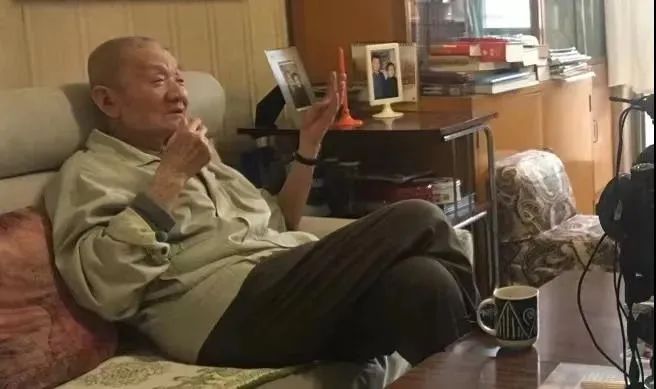

1. 问:我们中国舞美家最初是怎样与布拉格展览这样的国际大展建立起关系的?
答:当时我们与日本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日本的舞台美术学会经常与我们有互相的来往交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与世界舞台美术组织建立了交流,同时,中国舞台美术学会获得了许多海外华侨的帮助,能够更多地吸纳外界的技术与理念,随着中日两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国经常互相交换著作和往来办展,因此,他们邀请我们参加四年一届的布拉格展览,他们说,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可是欧洲人却没有系统地了解过中国的戏剧文化,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让中国的戏剧走到世界,而且,舞美学会相对独立性强一点,领导也愿意支持学会工作,多出去交流学习,也多为国内的艺术创作带回一些灵感。因为我经常负责与外界的交流,有的同志们外语讲的也不太好,所以让我来担任队长,带着当时的舞台美术设计,包括一些传统戏曲中的砌末、剧照、脸谱在1987年第一次来到布拉格。
2.问:可以说一下我们当时和日本戏剧界交流的情况吗?
答:最早,我们与日本的联系比较密切,当时在街上如果和外国人走在一起,会有警察前来问询(笑)。后来也有一些日本人来前来中国参观,他们主动提出,在戏剧事业上,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国最有国际影响力,我们应当扩大接触面和影响范围,集思广益搭建起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桥梁。
3.问:您个人在这种交流中有什么收获吗?
答:有一个日本人从中国的很多木刻板画或著作中,收集到许多关于戏曲的资料,其中就有广和戏楼。周贻白先生依据这本书还原了大量中国古代剧场,并且将图和翻译结合起来,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关于广和剧场的书籍。我对这本书一直有所怀疑,我认为日本人搜集的资料没有这么准确,果不其然,我到北京图书馆找到了那时候的一些书籍,是关于日本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戏剧,还有一本长卷,画的是故宫的北门到圆明园,一个皇帝过生日,举办了庆典活动,老板姓搭了戏台,办了庙会。我觉得日本人画的不像,他们都是从木刻板上拓下来的,而且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说在庆典里有很多妇女,在清代,是不大喜欢让妇女参加这类庆典的,那个时候正是徽班进京百戏融合的时候,很多东西画的很像,但也只是像,他们自己说是从中国的书籍里找到的资料。
其实那个时候中日两国的关系并不好,日本人想要来到中国风险很大,最早传播地方戏的一批人是从福建过来的,到北方的这一段距离从日本到中国的距离差不多,两国在佛教的信仰上是相同的,因此扬州的一群和尚也到日本去传教,日本人也很愿意接受,他们就从中国的书上截取、拼凑了这一段图像,但日本人对中国不太熟悉,比如很多剧目或多或少有一些角色上的出入,因此我也就发现了这些问题。那时,周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发现这些后,与戏曲界的人说了,戏曲研究院的人就来和我说,让我把写的这篇文章给他们发表。(笑)
4.问:在布拉格之前,我们国内的戏剧是怎样与国际接触到的呢?
答:1949年,我那时候刚从国立剧专毕业,第二年,我们剧专就和延安的鲁艺,还有华北大学一并组成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我在中戏的舞蹈团里做设计。新中国以后,北京成了首都,全国各地的文艺家才都来了北京准备大展身手,结果大家一看,嘿,这怎么全是破破烂烂的旧剧场啊,在这么大的北京,居然找不出一个能演出的西式剧场。事实是,当时的中国,即便是在上海那样的比较繁华的地方,能够算得上专业剧场的也屈指可数。比较有名的是兰心大戏院吧,但是兰心大戏院也不行,它只有剧场建筑,却没有舞台设备,而且它主要还是租给外国人、侨民用的。所以,建造新剧场、整修老剧场势在必行。我记得,从1950年开。就有了中戏的小经厂剧场、军委总政排练厅、军委总后礼堂,可是这些都因为缺乏现代剧场建设的专业知识,离国际上专业剧场的水平还差一大截。
到了1951年的时候,当时我才22岁,文化部组织了一个二百多人的文工团,带着我们的京戏、音乐还有其他领域的艺术作品,远赴欧洲考察他们的戏剧,欧洲人看了合不拢嘴。我们带了一个合唱队,一个交响乐团,都是音乐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去柏林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第一站到了德国,德国人非常热情,挽留我们演出和观摩了两个多月。第二站到了匈牙利,在和他们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合唱队的排法、各种舞台调度、舞台习惯都与欧洲接近,现在我们的舞台方式基本都是和欧洲学的。之后又去了波兰、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那时候有很多苏联部队驻扎在奥地利,借他们的场地请我们去维也纳演出。总之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了,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
5.问:当年中国舞台技术与国外的差距,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当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文艺和西方确实差距太大,与日本相比,我们确实对国际了解太少,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在舞台上用的吊杆我们只有三根,两根在上海兰心剧院还是坏的,所以在剧场装置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爬房梁,基本全是手动,栓上绳子、栓上滑车,到了欧洲发现他们全是电动的、机械的,平衡做得很好,非常方便,而我们的《白毛女》装台需要一整夜。总之呢,在国外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各个剧场考察,把这些剧院的大体构造、舞台机械、灯光设备的详细情况、参数都记录下来,还有好多剧场知识,回国后大家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剧场与舞台技术》。
我还记得在匈牙利演出的时候,他们的政党领袖在演讲,这时候距离观众入场只剩下一小时,这时候我们只觉得中国这么这么落后,连个吊杆也没有。他们的演出制度和我们不太一样,基本上是一天演一个戏,布景比我们多好几倍,没有机械设备就没法演出,我们看到之后,下定决心,回去几年之内,至少应该在全国范围普及手动的吊杆。回国之后,我们立刻和文化部反馈,说我们的剧场应该全面改造。
还有很多的东西,比如下雨的效果,我们中国下雨是在一个大笸箩里面装黄豆,噼里啪啦的声音倒是很像下雨,到了外国,发现他们是在机械里装一个类似中国烟筒模样的东西,从天顶到地面约有40多米高,中间焊着一根铁管子,里面有许多小铁片,上头有一个箱子倒黄豆,下面有一个类似弹簧的装置,一拉,黄豆就从里面掉下来了,下来的时候里面很多铁片,就会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特别像雨声,也比咱们那个国产的方便很多。国产的还有个毛病,就是喜欢用电动扩音器做效果,结果有很大的交流声音,非常虚假,包括国家大剧院也是这样。我让他们看我带回来写的记录,他们也不管,还用之前的方式,一听就是街上大喇叭的声音。
另外包括灯光控制,虽然用的德国的方式,买的也是德国设备,后来中国自己也做了吊杆什么的,但我们做得是不够的,当时有一个戏在这里上演,叫《乡村女教师》,很多下雨的场景,他们还是用扩音器,我们说话也不顶用,总是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结果他们发现我们还有点东西,慢慢的,各种国产设备也造出来了。(笑)
6.问:那您回国以后新的剧场建成了吗?
答:我回来以后太忙了,要教书,主要还要盖天桥剧场(始建于1953年的老天桥剧场,下同)。盖天桥剧场的必要性,是因为当时苏联有六个芭蕾舞剧和歌剧要来中国,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先盖一个能承载这些戏剧的剧场。虽然没有那么大面积,但也能容纳一千六百多人,舞台也比较符合国际尺寸。天桥剧场盖完后,连着演了六个戏,包括《天鹅湖》、《巴黎圣母院》、《叶甫盖尼·奥涅金》、《十月革命》、《多瑙河上的查布罗什人》《阿依巴利特医生》等在两个月内轮番上演。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完整地演出大规模的欧洲大歌剧和芭蕾舞剧,剧场不但要能容纳这六个大戏的全部器材,而且它的设备必须具有在三四个小时内更换一个大型布景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的剧场更换一个一般规模的戏也得一天左右。差不多从这以后,天桥剧场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和国际接轨的剧场,重要的歌剧舞剧剧目啊、重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啊,也大多在这里演出。毛主席亲自来观看了这六部剧作,我们中国的演员和创作者们虽然和苏联学习的时间很短,但卓有成效,因此在这一时期,又派了不少留学生出去学习外国戏剧,中国的剧场和舞台也都有较大的变化。宣传部的领导说,不管花多少钱,只要对创作、对演戏有帮助,就要花这个钱。
7. 问:您还参与建设了很多其他剧场,请再跟我们讲讲建设这些剧场时发生的故事?
答:我还参与了首都剧场、人民剧场、北京京剧院的建设,北京京剧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工人俱乐部,这四个剧场盖好了,文化交流就一下子疏通了,全国各地也纷纷开始效仿。一直到1959年,国家面临经济困难,所有剧场停建,中国第一波剧场建设热潮才收场。接着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旧宫去劳动改造。想起来觉得,下乡去也有好处,可以多了解一下农民和农业社会。作为一个创作者,你不到农村去,就没法真正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然后其他的各个地方的剧场,因为那时候没有钱,所以除了首都剧场有一个转台以外,别的都没有做机械舞台,也是四人帮倒了以后,中戏的逸夫实验剧场,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有车台、转台、升降台的舞台。但是由于我们是第一次做,另外中国当时的机械工业不过关,有很多东西,比如液压的东西应该同步的,两个应该升上去,完全齐平的,但是这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
以后慢慢我们学了国外的法子,现在都能够解决了。对戏曲来说呢,舞台设施已经算是另外一个东西了,戏曲认为这玩意儿没什么用处。所以盖梅兰芳大剧院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现在好了,经济发展起来了,大家只要觉得这个设备好,就算花再多钱也要购置,这样整个中国舞台就在器械方面发展起来了,到现在也算是大国之一了。
到了建造国家大剧院时,剧院请来一个法国建筑师,原来是盖飞机场的,并不会盖剧场,因此双方乃至三方爆发了许多次争吵。国家领导人为了照顾中法情谊,因此最后确定的还是法国工程师。最后全国选了三百多个和剧场相关的人来投票,看选择谁的方案,哪些地方必须改。过了个把月,这个事情才定下来,但还是会有分歧,比如剧场一定要有一个舞台美术工厂,我们本来设想的是,这个舞台美术工厂一定要在剧场内部或者是旁边,不能相距过远,也好方便运输,每天更换剧目,也省的花太多钱。最后国家大剧院方案定下来了,最后确定是在通州的台湖。虽然有很多好处,但也有缺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目前中国的剧场已经过剩了,现在各地盖剧院的热潮太高了,像是雨后春笋一样,风气也不太好,是争相攀比,你的豪华,那我就要更豪华。我一直认为,剧场最重要的不是它高不高、大不大,好看不好看,最重要的是对空间的合理利用,“合适”这两个字谁都知道,但要做到很难,我目前还没有在国内看到建造得那么恰到好处的剧场,大家钱花了不少,在设计上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说起来这也挺难的。
8.问:您也说了我们是器械方面的大国,那您认为在演出内容上呢?
答:这主要是我们的演出观念也在改变,以前都是现实主义,慢慢改变到一种多元并存的阶段,后来又回到了观众能看懂的地方。小说、戏剧都一样,先是模仿自然的东西多,写实的多,后来新的流派来了,观众们也看的莫名其妙,总之是写实的、抽象的颠来倒去。现在我一年多不看戏,就感觉跟不上了。
其实这也是与舞台技术相关的,就像最开始的时候,我不主张在传统大戏里面用写实的布景,因为传统戏曲它本身在艺术上已经太完整了,它就是假定的,就是程式化的,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它在世界戏剧中可算是独树一帜的,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它本来不需要的布景去破坏它的完整性呢?早年间有人做戏曲改良,把写意的东西全部去掉,在演出中把驴牵到舞台上,这合适吗?当然不行。可是后来,在下乡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看戏过程中有观众对布景很叫好,我们觉得这布景没什么用,它就是绘制了月亮的天幕或平面龙柱这类粗糙写实的背景,让舞台不那么难看,既不能推进剧情作用,也不能引导观众进入情境,甚至对戏曲中的移步换景有害。
但是观众们却很喜欢,所以我问自己,难道这些观众不感到“写意的表演”和“写实的布景”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吗?大多数观众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矛盾的、冲突的,他们长期处于审美方面的贫乏状态,简单的满足就足以遮盖这种矛盾,发现这一点后我就不再坚持反对在戏曲演出中运用写实布景了。在这个审美的大问题上,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做,得和广大的观众统一步调,不要总是给出华而不实的意见,而是要走到群众里面,实际地研究观众的需要,而戏剧舞台是为观众服务的,你的戏做出来是给观众看的呀,观众看懂了,觉得好,你就是好,观众看不懂,你做得再美再好看,那也是故弄玄虚,所以戏剧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观众身上的。
9.问:那么我们第一次去布拉格的时候,带的展品大多是写实的东西吗?
答:写实的东西有,同时也带了大量的戏曲程式化的东西,我们的要求就是,少带一些写实主义的东西,多带一些有民族色彩的东西。其实戏曲主要还是写意的,我们主要展示的还是服装和化妆,这都非常漂亮,外国人看了觉得又奇怪又喜欢,这些都是都合乎世界口味的。
9.问:您从布拉格回来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答:这一次完了以后,我就说我不去了,毕竟年纪大了。另外,老是我去也不好,别人没机会去。无论如何,这些交流还是让人很开眼界。回来以后,我被美国的大学邀请去教了四年书,实在累的受不了了,美国的大学问我,能不能晚上加一下班,有很多同学想要学汉语,他们说,要不你干脆别走了,我们给你办一张绿卡,就在美国生活吧。我拒绝了,我的老婆孩子都在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这一摊子事情交给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了,包括和美国人交涉。美国戏剧人对我们很友好,不像国与国之间的针锋相对,所以我们也请他们来讲课,办讲座,相处得很融洽。
9.问:您对以后参展的后辈们有什么教诲吗?
答:现在我们国家因为一带一路的关系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比较贴近,和非洲的关系也不错,还有人去非洲开讲座,加强交流,这些都是好的倾向,说明我们不断地走在开放发展的道路上。关于这个交流,既然我们收获很大,就应该继续下去,但我们还缺少几个敢担担子的人,希望勇挑重担的人越来越多吧。












